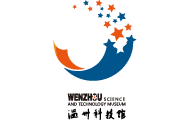酸湯,是苗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菜肴,所以,黔東南山區(qū)民間有“三天不吃酸,走路打撈穿”之說。
關于酸湯的起源,各地有著多種說法。而在下司的傳說中,“清酸湯”則起源于清水江航運黃金時期,距今已有一兩百年。
那時,承載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“兩廣”和“兩湖”貨物的千百船只由東而來,于此起岸,然后進入黔滇,而云貴兩省的土特產品集中到下司之后,亦由船只運達湖南洪江、常德,再過洞庭湖直達武漢、江浙。
據說,當時從湖南洪江逆水行舟到達下司,一般需要15天的行程。然而,由于江上往來船只密集,生活垃圾全部倒入江中,隨處可見從上游漂流下來的污物,河水受污較大,加上江水時常暴漲,所以,船上的飲用水必須自備。
于是,為了節(jié)約用水,船夫們經常將淘米水和洗菜水等,用水壇子積存下來,下次再用。
但是,時間一長,船夫們發(fā)覺用積存水煮出來的菜,竟有一種酸溜溜的味道。
開始時,大家很不習慣,有些人甚至產生嘔吐感覺。然而,船上條件畢竟有限,只要吃了不死人,人們也就“入船隨俗”。
但接下來奇怪的是,船夫們都覺得吃了這種酸水,非但不生病,反而對這種酸味產生依賴,以至于沒了酸味還吃不下飯。
久而久之,船夫們便發(fā)現這種酸味來自于積存水的自然發(fā)酵。它發(fā)酵時間不宜過長,以2至3天為佳。不然,過長發(fā)酵就會發(fā)臭。于是,大家用存水煮菜漸成習慣,最初的清酸——“存水酸”便出現了。
再后,“存水酸”逐漸在清水江沿岸流傳開來。其中,下司作為大碼頭,自然成為“存水酸”的登陸之地,進入了廚房。
隨后,“存水酸”在下司越傳越廣。人們在常年的實踐中,又逐漸掌握到用淘米水起酸的工藝,這使得湯液比以前更加清亮純正,因而稱叫“清酸”。
以后,又經過長期的摸索,聰明的下司人終于總結出“延用酸根、勤添米水、穩(wěn)定溫度、高溫殺菌、避免油污”等一套工藝。這種工藝,保持了清酸的穩(wěn)定。
下司人都很注意護養(yǎng)自家的酸湯。因為她們知道,不護養(yǎng)的話,酸湯就會酸敗,失去酸香味而變壞、變臭。因此,她們經常添加熱米湯。
當然,“清酸”湯液有了,但這只是吊湯的基礎原料。要想煮成上口的酸湯菜,還得有小白菜、瓜果、豇豆、西紅柿、豆芽等新鮮蔬菜,乃至于在酸味濃淡的調兌、菜素的搭配、佐料的選用、材料入鍋的先后以及煮沸時間的長短等,都得有講究。也因此,下司家家的酸湯菜端上桌來,湯汁如潭、菜素黃亮、酸香沁人、鮮嫩爽口。
至此,“存水酸”在下司演變成為一道獨特的“清酸”美味,飄香一地。
“清酸”湯雖為常品,但它在下司已經衍生出一道神秘的文化,有著一些不成文的民間規(guī)矩。首先,人們相互討要時,討要者不能揭壇自舀,而必須由送者揭壇舀給;其次,討要者只能說“要”或“找”,不能帶有“請”字。要是說了,或許遭到送者的婉拒;再次,討要者取得后,不能道謝,返身就走。要是謝了,送者也會不高興。人們認為,酸湯既然是最為普通的品料,不足為謝,禮請反而有傷人格。
說起下司酸湯的出名,還得感謝過去的幾位老阿姨。上世紀五十年代時,隨著下司成為湘黔公路上的一個重鎮(zhèn),往來就餐的旅客真是不少。“橋頭合作飯店”的這幾位老阿姨把酸湯菜煮得湯清菜亮,煮出幾大桶,任隨顧客們取食。于是,“到下司橋頭吃酸湯”成為來往旅客掛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話,從而一傳十,十傳百。
改革開放后,隨著人們對蒸煎燉炒的大魚大肉已經感到厭膩,精明的下司人于是推出清酸煮魚、酸湯梭肉等火鍋餐。這種煮法,食而不膩,飽而不厭,所以食客們蜂擁而至。由此,下司飲食業(yè)再次蓬勃興盛,由店而樓、而莊、而城、而街。每日,小車如梭,食客熙攘,座無虛席,逐漸將酸湯臻成品牌。人們只要提起下司,就會想起酸湯魚;只要想吃酸湯魚,就會想到下司。“酸湯魚”因此成為下司的代名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