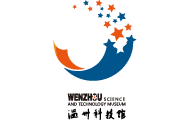要說(shuō)苗族酸湯,就得講凱里的酸湯魚(yú)。講凱里酸湯魚(yú),還得先提亮歡寨的酸湯魚(yú)。因?yàn)槊缱逅釡~(yú)如今聞名遐邇,亮歡寨是功不可沒(méi)的!我還在工作崗位上時(shí),一般有外來(lái)朋友,要吃當(dāng)?shù)靥厣模偷脦チ翚g寨。記得有一次,亮歡寨老板吳篤琴請(qǐng)我們一幫苗學(xué)會(huì)老者去為她“品酸”。那也是看中了我們這幫吃了一輩子苗家酸湯的老舌頭的“酸湯”敏感味覺(jué)。在苗寨里也有“品酸”的,不過(guò)那都是當(dāng)家的主婦和資歷特別老的老奶奶們的專(zhuān)利,我們男丁卻沒(méi)得資格,男人的舌頭是留著品酒的。
最近,有信息傳來(lái),亮歡寨申報(bào)并獲得了“國(guó)家級(jí)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名錄”,真是值得慶賀!這不僅僅屬于亮歡寨的榮耀,還屬于苗族,屬于整個(gè)黔東南。
其實(shí)整個(gè)黔東南就是個(gè)酸的王國(guó)。這里的各民族普遍都好這口酸。先來(lái)者在這里支起個(gè)大酸壇,無(wú)論你是先來(lái)的還是后到的,都將胃扔到酸壇里去泡,吃酸就像一場(chǎng)革命,舌頭的革命,既革命就不分先后。吃酸就成了黔東南的飲食特色,這樣的說(shuō)法應(yīng)該不為過(guò),因?yàn)槊珴蓶|說(shuō)了一句“不吃辣椒不革命”后,全國(guó)有好幾個(gè)省在爭(zhēng)著吃辣的呢:一個(gè)說(shuō)我不怕辣,一個(gè)說(shuō)我辣不怕,一個(gè)說(shuō)我怕不辣……你個(gè)小小黔東南爭(zhēng)不著。還是說(shuō)酸吧。
苗家酸湯魚(yú)是苗族特有的傳統(tǒng)佳肴。苗家的酸湯魚(yú)特指苗家用自家腌制的米酸(白酸)或糟辣酸(紅酸)來(lái)煮稻田飼養(yǎng)的鯉魚(yú),其味鮮美無(wú)比。注意,一定是煮稻田飼養(yǎng)的鯉魚(yú)!不然就不能算真正的苗家酸湯魚(yú)。
專(zhuān)家證實(shí),苗族是七千年前河姆渡稻作文化的創(chuàng)建者之一。苗族坡塘、稻田養(yǎng)魚(yú)歷史由來(lái)已久,苗族古歌中多次提及,《苗族史詩(shī)·砍伐古楓》就說(shuō),香兩老人在塘坎腳栽樹(shù),在塘里養(yǎng)魚(yú);然而,魚(yú)塘出事了,早上放進(jìn)九對(duì),晚上丟了九條,魚(yú)兒哪里去了?香兩這位大神很是惱怒,白天罵街,夜晚喊寨,也不指名。罵誰(shuí)呢?你那大楓香樹(shù)蔭自然涼快,白天家家都忙得很,只有紐兩家后生和尼兩家的姑娘正值青春期,他倆常在楓樹(shù)腳游方,把楓樹(shù)腳踩得溜光。
老人家,我們正正經(jīng)經(jīng)在游方。沒(méi)進(jìn)你池塘,沒(méi)撈你魚(yú)秧呀。
那又有誰(shuí)?香兩不由得順著樹(shù)干往上瞧,卻看見(jiàn)楓葉沾了一片白花花的魚(yú)鱗。香兩忽然明白了,好你個(gè)老楓樹(shù),我是一片好心腸,栽你在水塘邊,塘水養(yǎng)魚(yú)又養(yǎng)你。你怎么還安個(gè)壞心腸,不僅吃水還吃我的魚(yú)?
香兩老人家,怎么會(huì)是我偷吃魚(yú)呢?是從東方飛來(lái)的鷺鷥和雁鵝,翅膀?qū)挼孟駮裣_桿大得像竹竿,喙嘴粗得像脛骨。他倆天黑飛上來(lái),天亮就飛回。是他倆進(jìn)魚(yú)塘,撈走你的魚(yú)秧。
是鷺鷥和雁鵝?那你把他倆交出來(lái)。
天吶,那鷺鷥和雁鵝,一夜要走九個(gè)村,十六個(gè)地方去轉(zhuǎn)悠, 我哪里去尋?我的葉上沾魚(yú)鱗,我只靠根吸水,哪有嘴吃魚(yú)。
……
你說(shuō)你有理,我說(shuō)我有理,到底誰(shuí)有理,得請(qǐng)賈師理老來(lái)評(píng)判。要說(shuō)賈師理老,上方最出名的莫過(guò)金松岡,網(wǎng)朗臘,不過(guò)這理老耍大牌,騎一只雄虎,一到就要宰黃牛水牯,吃飽喝足才說(shuō)理斷案情。
還是請(qǐng)最實(shí)在的吧。請(qǐng)來(lái)休紐大神。休鈕不講究吃喝,一到就說(shuō)理。他帶來(lái)五把艾桿做的理片,“啪啪”,大神將理片拍在楓樹(shù)腳, 震得楓樹(shù)呼呼直搖。通匪藏賊你是窩家,有你留宿賊才來(lái),你不留宿匪賊走了,你還有什么理講!大神指著楓樹(shù)說(shuō)。
又爭(zhēng)論了好多天,楓樹(shù)有理辯不清,最終判下來(lái),要把楓樹(shù)砍倒,省得又有別的什么來(lái)借樹(shù)蔭干壞事。楓樹(shù)徹底無(wú)語(yǔ)了。
諸位看官,上面出現(xiàn)的這幾位大神都不是人類(lèi),他們是什么生物呢?我知道“休鈕”是犀牛,據(jù)說(shuō)犀牛角最堅(jiān)硬,再亂如麻的復(fù)雜案情都可以破。盡管我們的先人按照天地合一、萬(wàn)物同宗的觀念去對(duì)待他們,敘述他們。按現(xiàn)在人的觀念,這樣的判決是不合常理的。楓樹(shù)的冤屈是顯然的,但是,不合常理合天理,卻是符合后來(lái)發(fā)展的自然法則的,只有砍倒了楓樹(shù)之后,人類(lèi)才有機(jī)會(huì)誕生。這棵楓樹(shù)便是苗族的圖騰樹(shù),因?yàn)榭车沽藯鳂?shù),在其身上化出了千萬(wàn)物種。……鋸末變魚(yú)子,木屑變蜜蜂……最重要的是樹(shù)心孕育出蝴蝶,那可是苗族人歌頌的蝴蝶媽媽?zhuān)鍪€(gè)蛋,請(qǐng)樹(shù)梢變成的脊宇鳥(niǎo)來(lái)孵抱,就誕生了人類(lèi)的始祖姜央和雷、龍、虎等一干倒海翻江的眾兄弟……
還是說(shuō)魚(yú)吧,《苗族史詩(shī)·犁耙大地》說(shuō)姜央長(zhǎng)大后,犁田耙地養(yǎng)爹娘,田中養(yǎng)魚(yú)。由此可證苗族是古老的農(nóng)耕民族。苗族創(chuàng)造的農(nóng)耕文明之一就是稻田養(yǎng)魚(yú)。苗族稻田養(yǎng)的是鯉魚(yú)。
鯉魚(yú)的養(yǎng)殖歷史在漢典籍的記載里也有兩千年,我國(guó)最早的《詩(shī)經(jīng)》史篇記載:“猗與漆沮,潛則多魚(yú)。”朱熹集傳里云:“椮也,蓋積柴養(yǎng)魚(yú),使得隱藏避寒,因以薄圍取之也。”這個(gè)古老的護(hù)魚(yú)方法苗族還在沿用:即過(guò)冬時(shí),在水田里堆上一大蓬樹(shù)枝,以作護(hù)魚(yú)過(guò)冬之用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記載:秦漢時(shí)期,“楚越之地,地廣人稀,飯稻羹魚(yú),或火耕而水耨。”而苗族的祖先早在先秦時(shí)期就生活在“右彭蠡、左洞庭”之間,稻作漁撈文化已相當(dāng)發(fā)達(dá),“飯稻羹魚(yú)”正是苗族先民們的生活寫(xiě)照。
鯉魚(yú)在眾多的魚(yú)種里身價(jià)最高:神農(nóng)書(shū)里說(shuō):“鯉為魚(yú)貴”;宋代的蘇頌說(shuō):鯉魚(yú),“諸魚(yú)唯此最佳”、“為食上品”;古醫(yī)界稱(chēng)鯉魚(yú)為“魚(yú)中豬肉”;民間古諺語(yǔ)說(shuō):“洛鯉河魴,貴于牛羊。”傳說(shuō)孔子生了個(gè)兒子,魯昭公贈(zèng)送鯉魚(yú),孔子十分高興,將所生兒子取名為鯉,以伯魚(yú)為字。足可見(jiàn)鯉魚(yú)是農(nóng)耕民族最早認(rèn)識(shí)和飼養(yǎng)的魚(yú)類(lèi)。無(wú)怪乎苗族就認(rèn)定了鯉魚(yú),在苗族心目中,鯉就是魚(yú),魚(yú)就是鯉。
苗族先民創(chuàng)造了稻田養(yǎng)魚(yú),也創(chuàng)造了美味佳肴酸湯魚(yú)。這是苗族世代積累的經(jīng)驗(yàn),是苗族人民的集體智慧。苗家人自古以來(lái)就知道用酸湯煮魚(yú),在苗寨里,沒(méi)有誰(shuí)不用酸湯煮魚(yú)的。苗家酸湯魚(yú)經(jīng)過(guò)數(shù)千年的實(shí)踐與創(chuàng)造,形成了一整套特殊的傳統(tǒng)技藝,制作和烹飪工藝都十分講究。苗家酸湯魚(yú)蛋白質(zhì)含量高,營(yíng)養(yǎng)豐富,能幫助人體消化,消除疲勞,增加食欲,且能解酒,還能驅(qū)寒去濕,提高人體抗病和免疫能力等等。
苗家的酸湯魚(yú)與苗族人民的生活休戚相關(guān)。苗族各種祭祀活動(dòng)都少不了酸湯魚(yú)。凱里舟溪地區(qū)苗族每年的“吃新節(jié)”,祭祀祖宗的祭品是:12碗新米飯和12尾在酸湯里煮熟的鯉魚(yú);12年一次的鼓藏節(jié),客人的禮挑中,必有一串鯉魚(yú);過(guò)苗年的“年晚飯”祭祖供品就是酸湯煮的鯉魚(yú);農(nóng)歷二月二的苗族祭橋節(jié),必須用酸湯煮的鯉魚(yú)主祭;祭山神、楓木、石神,都用酸湯煮的鯉魚(yú)。
大凡在祭祀桌上的主祭品,必是與習(xí)俗的形成有關(guān),服飾研究專(zhuān)家們一致認(rèn)定,苗族服飾是其歷史記憶的載體,是穿在身上的歷史。魚(yú)紋是苗族服飾中最常見(jiàn)的紋飾,是構(gòu)成苗族服飾文化的重要內(nèi)容。在苗族觀念中,魚(yú)是繁殖的象征,是生命力的象征。那么,酸湯魚(yú)這一農(nóng)耕文明敬獻(xiàn)給后人的美味佳肴,已然苗家的鍋里煮了漫長(zhǎng)的歲月,在火里烤過(guò),在石鍋里煮過(guò),在陶罐里煮過(guò),今天是煮在鐵鍋里的。
說(shuō)酸湯,有幾個(gè)縣偏好紅酸,有幾個(gè)縣偏好白酸。紅酸白酸,各有所愛(ài)。說(shuō)起來(lái),白酸要比紅酸早,它的用材是淘米水或米湯,而紅酸用的是辣椒,辣椒傳進(jìn)苗鄉(xiāng)的歷史相應(yīng)晚得多。據(jù)說(shuō)印第安人吃辣椒在5000年前,15世紀(jì)末,哥倫布第一次到美洲,把它帶到歐洲,明代辣椒傳入中國(guó)時(shí)還當(dāng)著花卉欣賞,我國(guó)最早記載辣椒的書(shū)《遵生八箋》記載:“番椒叢生,白花,味辣,色紅,甚可觀”當(dāng)時(shí)叫“番椒”。最先吃辣椒的卻是貴州人,苗族一馬當(dāng)先。把辣椒用到極致。
苗族酸湯魚(yú)深受?chē)?guó)內(nèi)外客人的贊譽(yù),隨著改革開(kāi)放的春風(fēng)遍布大江南北,從昆明到北京、廣州、深圳,到處掛出凱里苗族酸湯魚(yú)的招牌;凱里苗族酸湯魚(yú)從民間走向高檔餐館,成為名菜;并由國(guó)內(nèi)走向國(guó)外市場(chǎng)。不過(guò)最正宗的還是苗鄉(xiāng)里農(nóng)家鐵鍋里的酸湯魚(yú)。